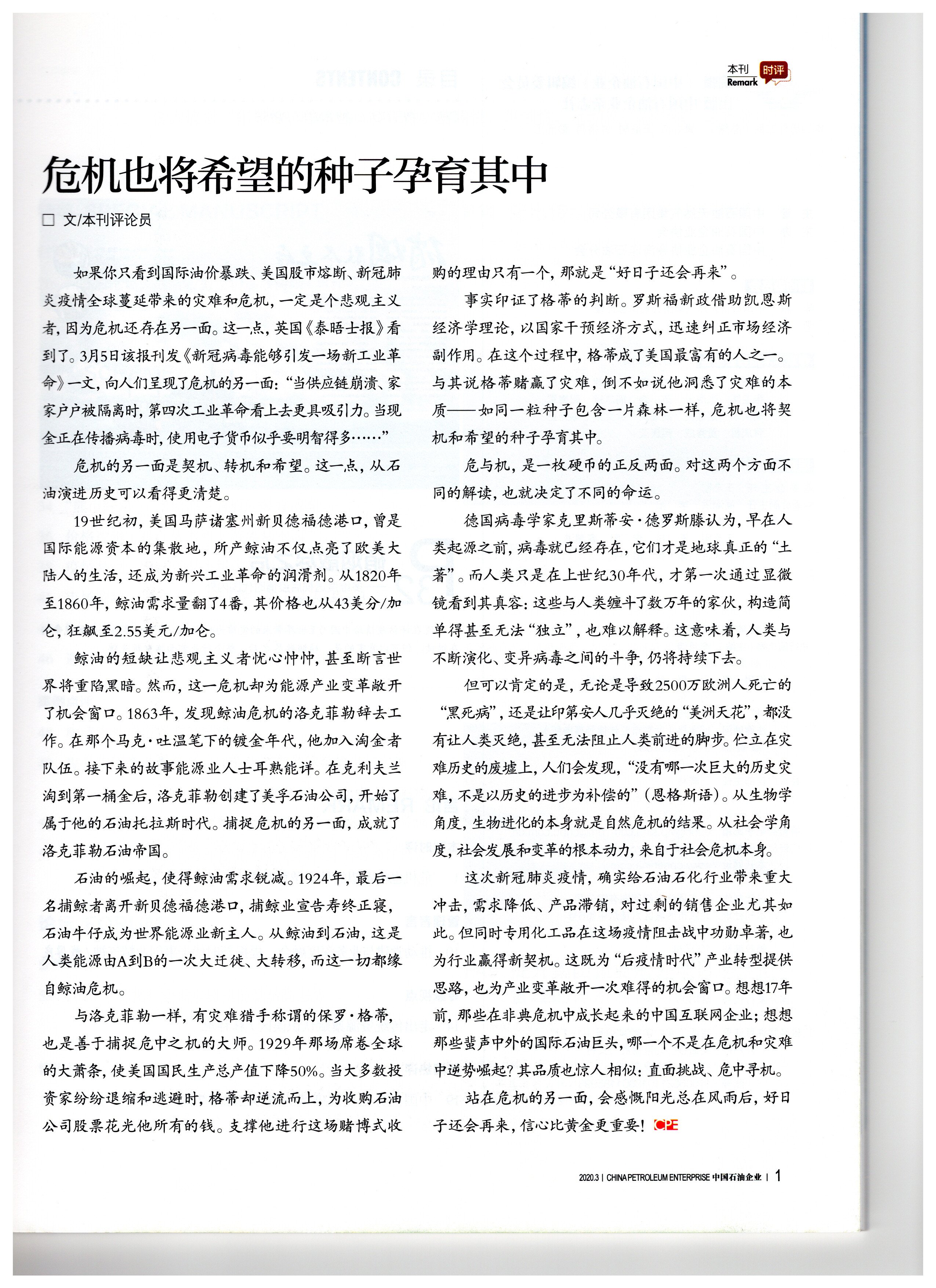如果你只看到国际油价暴跌、美国股市熔断、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带来的灾难和危机,一定是个悲观主义者,因为危机还存在另一面。这一点,英国《泰晤士报》看到了。3月5日该报刊发《新冠病毒能够引发一场新工业革命》一文,向人们呈现了危机的另一面:“当供应链崩溃、家家户户被隔离时,第四次工业革命看上去更具吸引力。当现金正在传播病毒时,使用电子货币似乎要明智得多……”
危机的另一面是契机、转机和希望。这一点,从石油演进历史可以看得更清楚。
19世纪初,美国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港口,曾是国际能源资本的集散地,所产鲸油不仅点亮了欧美大陆人的生活,还成为新兴工业革命的润滑剂。从1820年至1860年,鲸油需求量翻了4番,其价格也从43美分/加仑,狂飙至2.55美元/加仑。
鲸油的短缺让悲观主义者忧心忡忡,甚至断言世界将重陷黑暗。然而,这一危机却为能源产业变革敞开了机会窗口。1863年,发现鲸油危机的洛克菲勒辞去工作。在那个马克·吐温笔下的镀金年代,他加入淘金者队伍。接下来的故事能源业人士耳熟能详。在克利夫兰淘到第一桶金后,洛克菲勒创建了美孚石油公司,开始了属于他的石油托拉斯时代。捕捉危机的另一面,成就了洛克菲勒石油帝国。
石油的崛起,使得鲸油需求锐减。1924年,最后一名捕鲸者离开新贝德福德港口,捕鲸业宣告寿终正寝,石油牛仔成为世界能源业新主人。从鲸油到石油,这是人类能源由A到B的一次大迁徙、大转移,而这一切都缘自鲸油危机。
与洛克菲勒一样,有灾难猎手称谓的保罗·格蒂,也是善于捕捉危中之机的大师。1929年那场席卷全球的大萧条,使美国国民生产总产值下降50%。当大多数投资家纷纷退缩和逃避时,格蒂却逆流而上,为收购石油公司股票花光他所有的钱。支撑他进行这场赌博式收购的理由只有一个,那就是“好日子还会再来”。
事实印证了格蒂的判断。罗斯福新政借助凯恩斯经济学理论,以国家干预经济方式,迅速纠正市场经济副作用。在这个过程中,格蒂成了美国最富有的人之一。与其说格蒂赌赢了灾难,倒不如说他洞悉了灾难的本质—如同一粒种子包含一片森林一样,危机也将契机和希望的种子孕育其中。
危与机,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。对这两个方面不同的解读,也就决定了不同的命运。
德国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·德罗斯滕认为,早在人类起源之前,病毒就已经存在,它们才是地球真正的“土著”。而人类只是在上世纪30年代,才第一次通过显微镜看到其真容:这些与人类缠斗了数万年的家伙,构造简单得甚至无法“独立”,也难以解释。这意味着,人类与不断演化、变异病毒之间的斗争,仍将持续下去。
但可以肯定的是,无论是导致2500万欧洲人死亡的“黑死病”,还是让印第安人几乎灭绝的“美洲天花”,都没有让人类灭绝,甚至无法阻止人类前进的脚步。伫立在灾难历史的废墟上,人们会发现,“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,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”(恩格斯语)。从生物学角度,生物进化的本身就是自然危机的结果。从社会学角度,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动力,来自于社会危机本身。
这次新冠肺炎疫情,确实给石油石化行业带来重大冲击,需求降低、产品滞销,对过剩的销售企业尤其如此。但同时专用化工品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功勋卓著,也为行业赢得新契机。这既为“后疫情时代”产业转型提供思路,也为产业变革敞开一次难得的机会窗口。想想17年前,那些在非典危机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互联网企业;想想那些蜚声中外的国际石油巨头,哪一个不是在危机和灾难中逆势崛起?其品质也惊人相似:直面挑战、危中寻机。
站在危机的另一面,会感慨阳光总在风雨后,好日子还会再来,信心比黄金更重要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