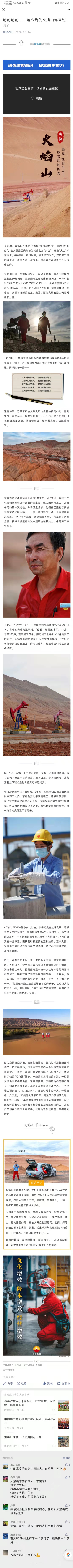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gPDgMbDnEPvKo0HH45_TOA
在新疆,火焰山在维吾尔语称“克孜勒塔格”,意思是“红山”,古人更是因炎热曾为其命名为“火山”,这座“火山”寸草不生。8月盛夏,红日当空,砂岩灼灼闪光,炽热的气流翻滚上升,热得人喘不过气来,是未曾去过这里的人无法体会的。
火焰山的热,热得极独特。一年只有两季,最热的时候气温超过50摄氏度,地表最高温度高达89摄氏度,一年中超过35摄氏度以上的日子在130天以上,是名副其实的“火洲”。30年前,吐哈石油人来到了火焰山,探寻深埋地下的秘密,唤醒了沉睡的油龙,激发了西北戈壁石油人无限希望和力量。
1958年,吐鲁番火焰山胜金口背斜顶部的探井胜1井试油喜获工业油流,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的包尔汉·沙希迪,闻讯赋诗一首——
这首诗歌,记录了石油人从火焰山启程的精气神儿。直到如今,在绵延百公里的火焰山下,近千名石油人仍然日日夜夜奋战在这里,体验着高温、记录着高温、战胜着高温。
在鲁克沁采油管理区玉北6钻井平台,正午2点,巡检工兰积虎和刘军背上一升装的大水壶,吃力地步行上山,开始午间的第一次巡检。井场没走几步,他俩的工服衬衣就被汗水浸透又瞬间晒干,一圈一圈白色的汗渍,让衣服看起来很脏。“水杯子不离嘴,永远都喝不够。”刘军扶了扶安全帽,被汗水浸透的头发一缕缕沾在额头上,像是剪了齐刘海儿。
玉北6一号钻井平台上,一座座抽油机威武的“站”在火焰山下,昂着头向着高温示威。“你看,那是玉北平7-17井,才来3年多,就晒成了灰色,旁边的玉北平11-12井是去年的新井,它鲜红的颜色就是7-17井曾经的模样。”兰积虎手指着火焰山脚跟儿下的两口油井,细数着它们对抗高温的经历。
晚上9点,火焰山上空太阳高悬,没有一点降温的意思。蒋书玲涂了厚厚一层防晒霜,戴上口罩,穿上防晒服,准备沿着上下班必经的戈壁滩边缘跑跑步。
蒋书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,6年前,在经历油田改革后她转岗来到了火焰山下的鲁克沁采油管理区。蒋书玲很感慨,自己竟然能坚守在这荒无人烟、气候极度恶劣的地方6年时光,还发自肺腑地爱上了这里。回忆起最难熬的夏天,蒋书玲目光变得温柔了起来。
4年前,蒋书玲的小女儿出生,孩子还没有过哺乳期,蒋书玲的返岗时间到了,看着襁褓中才4个月大的女儿,蒋书玲难忍离别,于是带着妈妈和女儿来到了火焰山下。4月的风没有一丝凉意,裹挟着砂石滚烫的直扑脸颊。还未入夏,火焰山下的日均气温已至35摄氏度,孩子小不能开空调,热得直哭闹。
白天,蒋书玲在工区上班,生怕听见风声。鲁克沁的风一起,火焰山上的沙土就被大风卷进了采油管理区生活点,满宿舍的土味儿,更是把高温一波一波吹进本已经闷热难耐的屋子,哄睡就成了蒋书玲最难熬的事。一个月后,蒋书玲把孩子带回哈密家中休假,再热的天气,孩子都不哭一声。“她是在火焰山经受过热浪考验的孩子,以后跟我们石油人一样,能耐高温。”蒋书玲站在宿舍窗前,看着不远处的火焰山,回忆着,笑着。
因为疫情防控原因,油田加强管控,鲁克沁采油管理区叫停了一切文娱活动,这让本就无聊的业余生活变得更加无事可做。下班后,李韬到食堂匆匆喝了几碗绿豆汤,就来到了他的“后花园”散步。一边是库木塔格的沙海,一边是火焰山东部绵延山体,这条巡检路,李韬和他的同事们每天不知道要走多少遍。李韬所在的东区采油中心,一个巡检工要负责30-40口油水井,巡检每两小时一次,一趟巡检十几公里。“即便什么活都不干,高温下沙漠跋涉几趟,腿都抬不起来。”李韬擦擦额头的汗珠子走得很缓慢,没了巡检时的匆忙,他拿着手机专注的拍摄起远处的山、井和自己印在戈壁滩上的影子,这是他工作结束后,最惬意的时光。
采访手记
火焰山到底有多热呢?我们的摄影器材工作十几分钟就耐不住高温被迫停机,航拍飞机飞上天没几分钟就报警返航,石油人却在太阳下,擦着汗,哼着曲儿,一趟一趟把不屈服的背影留给火焰山。
火焰山下蒸腾的热浪,热得人喘不过气。站在火焰山下,我们突然发现,火焰山如今的魅力,除了热浪、红山,最为重要的是,石油人开启的新纪元。勘探,探寻火焰山麓下的奥秘,开发,找出千万年来深埋地下的珍藏,工程技术,开拓进取给予助力……
巍峨的钻塔,轰隆的钻机,嘴里的号子,身上的劲头儿,谁说我们就无法“征服”这滚烫的火焰山呢。